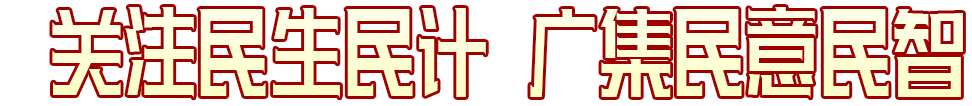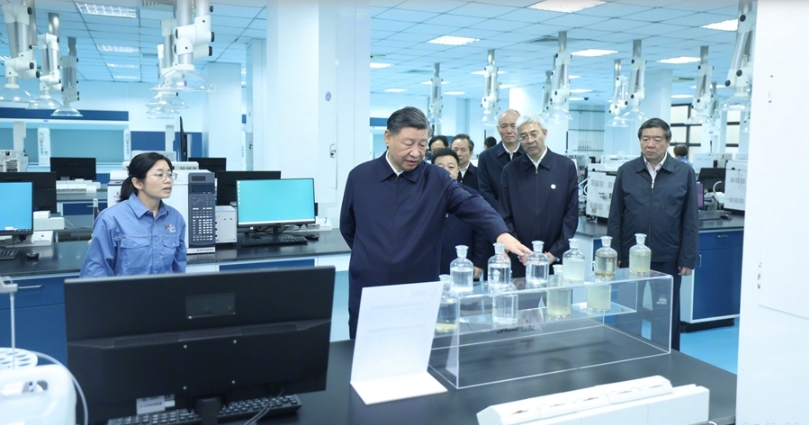一部《黑神话·悟空》带火了山西晋城的玉皇庙,四方游客蜂拥而至,观看出现在影片中的二十八宿。那确实是一组雕塑精美的文物精品,去年这个时候侄儿和侄女婿还特意带我去看过。侄女婿搞这个的,看过之后叫我发表意见,我说没有研究,不敢乱说。现在依然是没有研究,但有几点观感想提出来与各位交流,或许有助于将这个话题引向深入。
中国古代天文、律历、卜算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二十八宿,但没有办法深入研究的也是二十八宿。研究者普遍有种“老虎吃天,无从下口”的感觉,故翻来覆去多少年,始终是在原地打转。
症结在于人们在无意识中把“二十八宿”打包成了一个既定的、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,而不曾意识到,人类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、由比较片面到比较多面的过程,这个过程同时又是“二十八宿”理论由萌芽到成型、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和发育过程。研究二十八宿不首先确立这样一条掘进路径,后面一切的一切,都将无从谈起。
窃以为,目前成型的二十八宿理论以其生成过程划分,大致可以分作三段:左青龙右白虎等所谓“四象”,应该是战国年间的产物;人格化的二十八位“星官”,什么亢金龙、斗木獬之类,一望而知是出自底层道士之手,论年代不会早于汉朝。剥离了这两部分以后,剩下的“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”等,才是原汁原味的二十八宿,才应该是追根寻源的重点。
那么,原汁原味的二十八宿最早是出自何时、何地、何人之手呢?个人认为,其萌芽出自昆仑山上、四千年前,防风氏及其继任者望获(天皇氏)一脉是具体的操盘手。我这样说的理由,除拙作《发现虞朝》中已经列明的相关线索以外,尚有如下一些补充说明:
一,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等二十八个字,除去个别例外(如“房”和“张”就当是“方”和“长”的衍变),都是我们在《发现虞朝》里见识过的那个年代的“熟字”。而当年还不成器的“龙”,反倒没有进入二十八宿。
二,对古人而言,描述无限太空中的对象必须借助于有限地面上的事物。例如,太阳运行的四时八节就不是标记在天上而是标记在地上,昆仑六峜中一字排开的“五指丘”就足以将其描绘得清清楚楚。同样的,以二十八天为一个周期的月亮的运行轨迹,最初也不是标记在天上而是标记在地上,那便是昆仑周边的二十八个地名、方名抑或山名。不妨设想这样一幅场景,假设我们自己就是混沌初开的古人类,在位于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上日复一日观察月出,我们会怎样形容月亮的位置呢?十之八九会是这样:它昨晚这个时候出现在蛇口码头的上空,今晚这个时候出现在红树林的上空,明晚这个时候将出现在车公庙的上空……诸如此类。总之是拿自己和别人都熟悉的名词做参照,而不会自己去生编一套谁都没见过的字符来做标签。与今天的我们显著不同的是,古人给事物命名是以单字居多,于是,我们看到了以单字命名的“二十八宿”。
三,二十八宿里的那二十八个单字,会不会是当年的地名、方名抑或山名、水名呢?从鄙人探秘连山的过程来看,结论是肯定的。例如,“心”是沁河,“房”是风方,“井”是河津,“角”是古昆仑南侧、今杨柏大峡谷与东阳河(横河)相交形成的那个著名的大夹角……月亮每天悬停于一个地方的上空,那一溜的地名就成了标记月亮轨迹的方便工具。再后来,到了需要给满天星斗命名的时候,地上的那一串名字才投射到天上,在月亮的移动轨迹旁才出现了心宿1、心宿2,或角宿1、角宿2,等等。就是说,不是月亮“借宿”于星宿,而是星宿借月亮而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。
四,还有一点需要说明:二十八宿最初理当是一条半明半暗的弧线。战国以后,随着“四象”观念的加入才逐渐演变成环视星空360°无死角的圆盘。两汉以后尤其是两宋以后,又渐次有了更加细分也更为复杂的描述系统。到南宋石刻天文图(也叫““三垣四象二十八宿”图),与早期的二十八宿概念就已经判若鸿泥。也因此,后来的二十八宿与真实的月球轨迹渐行渐远,二十八位“星官”更是有了自己完全独立的“生命”轨迹,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