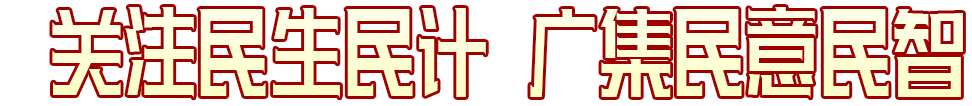甄老愚是个痴迷于文学创作且眼眶子又非常高的家伙。他写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,什么这文学公众号啊,那文学网啦等所有的电子媒体平台都不在他眼里,非要在纸媒上发表不可;在纸媒上发表还要上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当代》等国家级文学期刊,在市以下刊物上发表都觉得掉价儿。但许是眼高手低,许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,他坚持不懈地写了23年零8个月又21天,发送和投寄短篇小说111篇、诗歌222首、散文333篇,可除了得到“大作已收到,三个月接不到通知请另投”等千篇一律的电子回复外,一个字眼儿也没给刊用。其中,《当代》所公布的投稿邮箱和《解放军文艺》的散文、诗歌、非虚构等栏目投稿邮箱就根本发送不进去。电脑桌面虽然显示“发送成功”了,但打开收件箱全是“系统退信”。甄老愚气得直跺脚,他奶奶的,这哪是为了方便作者投稿啊,分明是在耍花招儿,瞪着眼睛坑爹嘛!稿件压根儿就进不了编辑部,或者虽然进去了,但编辑根本不予理睬,怎么能在上面发表文章呢?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?再说,你登出来的作品真好也行啊,全是让人看不懂的东西。无论小说、诗歌、散文,还是别的什么文学作品,至少能让读者看得懂,知道你说的是个什么问题,说的是什么事儿,让读者看后有点儿印象,那怕是谁记住其中的一句话也行。连句话都让人记不住,还堂而皇之地登出来,把好的作品挤掉,太他妈的那个了。这天,他选了几篇自认为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,到打印店里打印出来后,拿着去请教漂白粉:一是让她给出出主意,二也放松一下快要撕裂和崩溃了的心。
漂白粉和甄老愚原来都在县物资局工作。那时,甄老愚是文秘科科长,漂白粉是该科科员。因工作关系,二人日久生情,成了相好的。后来物资局不景气,漂白粉下海经商去了,甄老愚则辞职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。20多年下来,漂白粉凭着自己的绝佳姿色、灵活的头脑和能说会道的嘴巴,不但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做大做强,成了千万富翁,还勾挂八方,政界、商界、文化艺术界、出版界、教育界、医疗卫生界等,都有她的熟人和朋友。用她自己的话说,世上没有她不认识的人,也没有她办不成的事。甄老愚想,尽管漂白粉的话有不少自我吹嘘的成分,但她毕竟见识多,路子野,叫她给参谋参谋,或许能有个峰回路转。这天,他骑上自己的那辆除了铃铛不响,全身都响的自行车,一步三摆动地赶到了漂白粉的住处。
这是一座180平方米的豪宅。10年前,漂白粉与丈夫离了婚,唯一的女儿判给男方后,就一直没有再婚;而甄老愚呢,老婆子实在不愿意跟他过靠低保生活的穷日子,更受不了他一天到晚趴在电脑桌上码字儿,不挣钱还消耗电脑和电费,便趁甄老愚埋头写作的当儿,带着唯一的儿子跟一个杀猪的跑了。二人都是单身,虽没有登记结婚,也不在一块儿居住,但早已成了事实上的夫妻。漂白粉每月打给甄老鱼五千块钱;甄老鱼则每周一次到漂白粉处过夫妻生活。大家都羡慕甄老愚处了个好对象,暨发给工资还满足生理需求,他也说是是是。可一旦喝醉了酒,他又说,我们是男的卖淫挣钱,钱女的付费嫖娼啊!他还是放不下身段,低不下作为文人的高贵的头颅。
“老漂啊,”一番云雨之后,甄老愚开始向漂白粉倒开了苦水。“当时咱俩双双离开物资局时,你表示要在商界出人头地,我扬言在创作上一鸣惊人。如今20多年过去了,你出人头地了,可我,别说惊人了,连个响屁都没放出来。他奶奶的,急得我想死的心情都有,别说到你这里来干男女之事了。”
“你刚才干得不是很带劲吗?”漂白粉揶了甄老鱼一眼,“我看看你都是写的啥、咋写的?”
甄老愚把文稿递过去,漂白粉手沾唾沫,一页一页地看起来。“咦——难怪你父母给你起了个老愚的名字,看来,你真是个大老愚啊!”漂白粉边看边糟践他,“别说人家不用你的稿件,叫我是这些刊物的编辑,也是不会用你的这些糟烂玩意儿的。都什么年代了,还英雄人物式的写法。你以为,现在的文学作品还是教育人民、团结人民、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啊?不是了,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,就像青楼里的妓女和红楼里的鸭子一样,是被有钱人用来玩弄的、娱乐的、满足心理和生理需求的。既然是用来消遣的,那就就要有刺激性,吊人的胃口,叫人愿意看,有卖点。比如写写吃喝了,拉尿了,丰乳了,肥臀了,调情了,交配了,往酒缸里撒尿了,当官的把小孩子煮着吃啊,等等。像你这样一脚踢死一个黑社会头子,三拳打死了他的三个小喽啰;再不就是为了干好工作,三个月没有回过家,连孩子的生日都忘了,造成两口子不说话,不干那事,最后离婚,云云,这都不行。你的写作理念太落后了。”说着,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名叫《血城》的长篇小说,叫甄老愚拜读、学习、借鉴。并说,这是一部当代著名作家的新作,很是热门。
“噢,是吗?”这时该甄老愚边看边思索了。他一口气看了五章半,似乎明白了一点儿什么。他想,尽管漂白粉说得有点极端和绝对,但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小说是写人的,既然写人,那就要写得像个人。不吃喝,不拉屎,不尿尿,甚至连婚都不结,一心扑在工作上,不食人间烟火,这不是人,是神,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里的男女主角不都是这个样吗?记得改革开放之初,自己还曾写文章批判过这种现象,说这是极左遗风,应该彻底清除。怎么到了自己创作的时候,又犯同样的错误呢!他后悔上中学时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林海雪原》之类的小说看的太多,领会得太透,掌握得太牢,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笔法运用在现在的创作实践上;更后悔这些年来没有及时关注文坛发展变化的新形势,没有和一些文学大家们交流交流。这不,白白地浪费了二十多年的功夫,还搭上了老婆和儿子。叫我老愚,确实是名副其实啊!甄老愚在心里恨恨地谴责自己。
“老漂啊,”甄老愚的脸由阴转晴,“这个创作理念的重大变化,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,叫我白忙活了这么多年。”
“怎么没告诉你啊,早告诉过你。可你就是不听,说写的东西要有正能量,要反映人们普遍关心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,不能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倔得跟头驴似的。你看看,现在的文学作品,哪个反映现实了?是《红高粱家族》反映了,还是《人生海海》反映了,抑或是《软埋》反映了?人们愿意看,卖得出去就行。你非要认那个死理儿,怨谁啊?”
“好,怨我,怨我,我承认,现在彻底承认。”甄老鱼虚心接受漂白粉的批评指责,“不过,要是按照你说的,光写调情了,交配了,往酒缸里撒尿了等,不发表还好,万一发表了,人家骂我流氓怎么办?你看莫言、贾平凹他们,人们骂得多难听。”
“谁让你光写那些东西了?要写人的本真,本真懂吗?你不是曾说过,人有什么两个性?”
“两重性。”一说这些,甄老愚又长起脸来了,他居高临下地说,“就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。社会属性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而不是狗啊、驴啊等的特性,也就是善的一面;自然属性就是动物性,跟狗啊、驴啊、狮子、老虎啊等一样,也要吃喝拉散、调情交配,甚至强奸轮奸、杀人放火等等,也就是恶的一面。”
“对对对,两重性。”漂白粉也拿出居高临下教育人的口气,“写人的时候,要把这两性都写出来,不能只写一性,放弃另一性。写好人呢,多写社会属性少些自然属性;写坏人呢,则反过来,多写自然属性少些社会属性;写平凡的人呢,两性半对半。总而言之,要把人写得像个人。像神一样不行,像动物一样也不行,介于这二者之间。”说到这里,漂白粉停顿了一下,继续教导,“还有,你还选择那明确的主题,编造那完整的故事,制造那激烈的矛盾冲突,一环扣一环地演绎,这也不行!现在时兴意识流,脚蹬踩西瓜皮,滑到哪里算哪里,全是写人性,写人性的善恶美丑,人性变化到哪里,你的笔头子就跟到哪里。你看《血城》是怎么写的。”
“噢——”甄老鱼又翻了几页《血城》,似乎是完全明白了。他扑上去,抱住漂白粉在她脸上整整啃了十一口。要不是漂白粉此时不愿意做,又得把她按在沙发上再云雨一番。“他妈的,埋头写了二十多年,还不如你这一阵子的批评教育。看来,我还是来得太少了。有空多来几趟,多听你叨唠叨唠,或许我进步还快一些。”
“那你就经常来呗!”
“来!”
半年后,甄老愚的短篇小说《花朵 》出手了。他比照着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当代》等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反复欣赏,越看越自我感觉良好。不但写了主人翁如何爱岗敬业,诚实守信,主持正义等,还根据情节发展变化的需要,恰如其分地写了她如何吃饭,如何拉屎尿尿,如何跟自己的男人睡觉以及如何与别的男人偷情等。为了突出小说的张力,还充分吸收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,一忽儿出现了一个大美女,一忽儿又看到了人咬狗的画面,一忽儿又游到了大海深处与鳄鱼嬉戏,一忽儿又在雪地上尿个坑等等。你看,多像漂白粉推荐的《血城》一书,比不上若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,与茅盾文学奖、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相比,我看不相上下。诶,这样的精品力作哪家刊物要是不给刊用,只能证明这家刊物的编辑外行,不识货。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从国家级刊物到地方刊物、从本省本市的刊物到外省外市的刊物,他先后向六家编辑部发出,均石沉大海。一家刊物等三个月,六家刊物白白地等了十八个月。甄老愚沉不住气了,又来找漂白粉商量对策。
“怎么,大作发表了?”漂白粉正侧躺在沙发上撸猫,见甄老愚进来,她停止了捏猫的耳朵。
“发表他妈的个逼!”甄老愚使劲儿把文稿摔在茶几上,“你说要写人的本真,既写出力干活儿,又要写调情交配,这不,我写了,把咱俩背后干的见不得人的事都当做素材写上了。但还是白搭!弄得我这一年半都没心思往你这儿跑,光等着编辑部的最终回话了!”
“我看看写得咋样。”漂白粉把文稿抓在手里,边看边评估,“行啊老愚,写得不错嘛,既有正能量又耐看,按说应该能给刊登啊?”
“可就是不给登,你有什么办法!”
“最后这一次,你发给哪家刊物了?”
“国家级、省级都不行,最后我发给咱们市的《太空文学》了。”
“噢,《太空文学》啊!这样吧,你说好不算,我说好也不算,咱听听《太空文学》主编的意见好不好,人家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啊!”说着,就拨通了《太空文学》的主编贾文明的手机。
“贾哥耶——”尽管徐娘半老,漂白粉的喋声听起来还是很令人心动,“我的一位表哥兼老领导写了个短篇发你们《太空》了。我看写得不错,能不能给用一用啊?”
“真表哥假表哥啊?”看来二人的关系确实不一般,“你的表哥也太多了,别有了年轻的表哥就把我这个年老的表哥忘了哦。”
“看你说的,有了再年轻的表哥,也不会忘了你这个的主编表哥呀。”
“没忘就好,我可是时刻想着你这个妹妹的。说吧,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。”
“我这位表哥兼老领导写了一个短篇,名字叫《花朵》。向你们《太空》发去三个月了,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你们究竟用还是不用,给个囫囵话也行啊!”
“噢,你说的是《花朵》啊,有印象,有印象,确实写得不错。可这个作者好像连个市作协会员都不是,我如果用了他的作品,圈内的人有意见啊!”
“这么说,他首先得入会,成为咱们市作协的会员才行?”
“对。”
因漂白粉把手机打在了最大音量上,甄老愚听得清清楚楚。“入会,”他撇了撇嘴说,“入会得有公开发表的作品才行,他们不用我的稿子,我没有作品,怎么入?再说了,入会得缴会费,我一个月300块钱的低保,要不是你资助,吃饭都成问题,哪有钱缴会费?”
“嗨!”漂白粉一拍大腿,“国家、省级的作家协会不好加入,小小的市级作协的会员还不好办?包在老娘我身上!”
估计又是漂白粉的绝佳姿色和金钱起了大作用,不过一个星期,甄老愚加入市作协会员的手续全部办妥,比在游乐园里玩漂流顺流而下还利索。有了作家会员的头衔,《花朵》很快就在《太空文学》上刊登了,并且放在了头题。在这期刊物的开头语中,编辑还把《花朵》好一番赞扬,夸奖其理念超前,引领了时代新潮流。
按理儿说,多年的心血有了结果,甄老愚应该高兴得把漂白粉掀倒在床上忙活小半天,然后再找个烛光里的妈妈酒店庆贺一番才是,可他却没有这种心情。这算什么事儿啊,他想,哪家刊物都标榜自己不厚名家,不薄新人,可同一篇作品,圈内人写的就重重地采用和推介,圈外人写的就置之不理。什么要培养新秀,什么要开展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,什么要发展党的文化事业云云,原来都是用来糊弄我们这些大老愚的啊!都说文坛是一方净土,去他娘的,我看比他妈的官场还腐败!什么编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狗屁,人类灵魂的腐蚀者还差不多!甄老愚脸上阴沉得像是要下雨。
“怎么,作品发表了还不高兴?”看甄老愚的脸耷拉得比驴脸还长,漂白粉有些不解。
“叫我怎么高兴啊!”甄老愚继续刚才思考的话题,“老漂啊,你见多识广,比我的社会经验丰富,你说说,现在要办成一件事,不走歪门邪道不行吗,难道走正道就办不成?”
“这要看哪个领域哪方面的事儿了。现在通过强力反腐,官场上是比以前好多了,但文化艺术领域还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,难道文化艺术就不归共产党领导?”
“归是归,可是不好监管啊!”
“怎么不好监管?”
“拿我来说吧,我是经商的,属于商业领域。我卖的胸罩,档次最高的标价一百二十块钱一条。有人购买时就是一百二十块钱,多收一分人家就不愿意,甚至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你,有个明确的标准。小说有什么标准?只要政治上不反动,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是很大,至于艺术性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看法,最终只能由编辑说了算。既然最终由编辑说了算,那就看编辑的了。这自然就印证了过去常说的那句话: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,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,不服不行。”
“那宣传文化部门是干什么吃的,他们就不能制定几条规则来规规他们?”
“问题是,现在是专家说了算啊。没听说吗,专家治校,专家治院,专家治所,你要是管他吧,他说你是外行,外行插手内行的工作是瞎指挥,不懂文学创作规律,他还要反你的腐败呢!现在,专家厉害啊,如医疗卫生方面的专家,可以左右国家的防疫政策,叫你打疫苗、做核酸你就得打、就得做,尽管明摆着不管用。”
“那就没办法了?”
“没办法!”
“无解?”
“无解!”
谈到这里,甄老愚的心情愈加沉重。“他奶奶的,管吧,是外行领导内行,是‘文革’遗风,不行;不管吧,又没有鸡巴正事,也不行。这叫我们这些底层的文学爱好者如何是好?难道都像你一样去经商赚钱办企业?”
“也未尝不可嘛,你跟着我干就挺好,省得我给别人开工资了。”
“你是知道的,我压根儿就不是经商的料,也不喜欢经商,只愿意耍耍笔杆吹牛逼。这牛逼吹不成,我活着还有啥用?”
“别灰心丧气嘛,这不有成绩了吗,《花朵》就是一个大成绩。”
说到《花朵》这个大成绩,甄老愚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些。是啊,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管它正道歪道,能发表作品就是好道。有漂白粉在前面趟路子,我只管写就是了。不但要写,还要写出精品来。当年辞职时,曾向领导和同事们夸下海口,要写出一鸣惊人的传世之作。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,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为了在《花朵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,上省级、国家级刊物,他几乎每天都泡在省市图书馆里,把所有的纯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和近几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,一篇一篇、一本一本地细细研读,从中领会人家的创作理念和笔法技巧。听说《金瓶梅》写男女之事很到位,竟豁上一个月的低保金,到书店里买上全套的《金瓶梅》,一遍又一遍地粗读、细读和精读。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感,他冒充打工者深入到屠宰场体验生活,看看注水猪肉是怎样制造出来的,结果被屠宰场经理识破,竟把他当做公猪劁去了一个蛋子。多亏他反复亮明身份,双方才知道,当年他的老婆就是跟眼前这个杀猪经理离家出走的。看在二人曾睡过同一个女人的份儿上,并在甄老鱼写下保证书,申明只是为了写小说,绝不曝光屠宰场给肉注水的秘密,更不状告杀猪经理和自己法定妻子犯重婚罪的前提下,人家才刀下留情,没有把他的那个蛋子连同老二全部摘除,否则他永远就不能跟漂白粉在一起了。经过大半年的努力,又一短篇小说《春花》杀青了。不但他自己看着满意,拿给漂白粉看,漂白粉也说比《花朵》又进了一大步。
“你准备发给哪一家刊物啊?”漂白粉问。
“全国规格最高的,《宇宙特刊》。”
“好,我找他们的牛主编。”
“行啊老漂,国家最高规格刊物的主编你也认识?”
“当然了。你这半年多不是泡图书馆就是进屠宰场,弄得老娘好生寂寞,我只好到京师去散散心了。”说着就拨通了牛主编的手机。实际上,漂白粉是在暗中帮助甄老愚。
看着漂白粉喋声喋气地跟牛主编通电话,甄老愚的心里可谓五味杂陈。他娘的,为了能在纸媒上发表篇作品,事实上的妻子跟别人睡觉,自己不但不能有半点儿怨言,还得坚决支持、完全赞成、彻底拥护;法定的妻子跟人家跑了呢,不但不能说半个不字,还得写下保证书,不能曝光人家往猪肉里注水,不能状告人家犯重婚罪。你看这绿帽子戴的,一顶还不行,还得带两顶。我甄老愚都成了什么了?缩头乌龟一个!唉,窝囊啊,实在是窝囊!
“妹妹啊,”漂白粉的手机里传来牛主编哭穷的声音,“不是大哥不给您面子,更不是不念及咱俩的床笫之欢,我得为手下十几号人的吃饭问题着想啊。现在不比从前了。过去办刊物是财政拨款,现在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,大哥我需要钱啊!”
“你说,怎样才能上你们的刊物吧!”
“两条:一是订购我们的刊物500份,年年订、月月订;二请作者出专辑,刊物由作者包销,我们从中提取费用。”
“写得好也不行吗?”
“写得再好也不行,除非是莫言、铁凝、池莉、迟子建等人的作品,能给我们的刊物带来卖点。”
其实,还有一条牛主编没有说出口,那就是无非你是哪家杂志社的编辑,你用我的稿,我用你的稿,以刊谋钱,达成名利互换。
“哎吆,”听了这话,漂白粉也有点而激动了,“这么说来,你们干脆明码标价不就得了,像职称论文那样,一个页码多少钱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多痛快啊,何必拐那么多弯子?”
“我的好妹妹呦,那我们还是人民的刊物吗?社会舆论我们也受不了!”
“嗷,原来你们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啊!敢情是文化人,比我们这些粗人想得周到、细致、全面。”
“干嘛把问题说穿呢,像咱俩上床的事,能公开说吗?”
……
放下电话,漂白粉也傻眼了。她也没想到,一贯给人以神圣纯洁高尚印象的文坛,竟把商业规则运用得这么娴熟充分,竟充斥着这么浓烈的铜臭味,比我经商做买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回头再给本市的《太空文学》贾主编打电话,贾文明也是这么一副腔调,并说,《花朵》那一篇就是看在你跟我睡觉的份儿上勉强刊用的,不能再有第二次了,除非大量订购我们的刊物。
“他不是咱们市作协的会员吗?”
“会员更应该带头订购!”
漂白粉没辙了。他娘的,喝酒、上床的时候一个个都像发了情的公鸡似的,拍着胸脯说没有问题,到了真事上都成草鸡了。不过也不能怪人家,编辑也得吃饭啊!就像医院里的医生、护士一样,病人都不缴检查费、医药费,他们怎么发工资、奖金?作为一个商人,漂白粉太懂得这些明的、暗的和半明半暗的潜规则了。听说有人评职称,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要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块钱,与那些专业核心期刊相比,无论是贾大明还是牛主编,要价还算低的呢。原来骂人家腐败,利用刊物搞权钱、权色、权权交易,看来是错怪了人家。没钱怎么办刊啊?就像我一样,没钱怎么做买卖!
“老漂啊,”看漂白粉又陷入了苦闷之中,甄老愚用安慰的口气问她说,“你说各级文学刊物都是干什么用的?”
“娱乐消遣的嘛,我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说了吗?”
“我是说他们在公开场合讲的,就是办刊宗旨是什么?”
“教育人,鼓舞人,让大家心灵都变得美好而不能变得丑恶,用当前官方的话来说,就是教育引导和激励人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。”
“既然如此,国家就应该给他们拨款才对啊,怎么能让他们如此做买卖?”
“我的老愚啊,”漂白粉简直是苦口婆心了,“国家需要钱的地方多了去了。你难道就没听说,有的地方政府部门给公务员发工资,都是借钱发的哩。公务员的工资都是借钱发,哪还顾得上消遣娱乐的文学刊物?做梦去吧!”
“那就没办法了?”
“没办法!”
“没解?”
“没解!”
此时,甄老愚的脸痛苦得都扭曲变形了。他不住都唉声叹气,连说这咋办,这咋办。一双骨瘦如柴的手,不停地来回搓揉。
“这样吧,”看甄老鱼如此痛苦,漂白粉又安慰他,“我订他们的刊物,你在上面发表文章,怎么样?”
“那不还是花钱发表作品吗?花钱发表作品还算本事吗?这和经商做买卖有什么两样?”
“老愚啊老愚,还钻那个死牛角尖。现在办刊就是做买卖,你以为真发展文化事业啊!”
“那你问问牛主编,少订点儿行不,订个是十本八本的。”他不愿意欠漂白粉更多的人情。
漂白粉尽管不愿意再给牛主编打电话,但为了甄老鱼能够发表作品,还是咬咬牙运运气拨通了牛主编的手机。一是出于二人事实夫妻的感情,二是他认为甄老鱼的小说确实写得好,不发表太可惜。
“牛哥啊,这样行吗,少订购点儿你们的刊物,订个十本八本的,怎么样?”
“哎呀,我的好妹妹,我不是跟你说了吗,我们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,不是财政拨款。还有一个情况你有所不知,我们有的编辑是打工的,不在编,我不但得给人家发工资,还得给人家买五险一金呐!你不是大老板吗,大老板还在乎这几个钱?我跟你上床套近乎,就是想让你多订我们的刊物。”
“看来不行啊老愚,”漂白粉放下手机。“你靠刊物出名,人家还靠刊物活命呢!人家比你还着急。”
“不订不行。”
“不行!”
“还是没解?”
“没解!”
“他们可以卖刊物挣钱嘛!”甄老愚简直疯了,他跳起来吼叫,“光从我们这些没有钱的文人身上打主意,算什么本事?”
“哎呀老愚,你吓住我了。”漂白粉也提高了嗓门,“除了像你这样的所谓文人,想发表自己的作品,才看他们的刊物,有的人看也是只看登有自己的那一篇,别的人谁看啊!你到省市图书馆看看去,看看书架上有没有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,图书馆就根本不进这些货。告诉你吧,现在的年轻人就不知道纸质刊物为何物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网络发达呗,一分钱不用花,什么文章都看了,谁还花钱订购他们的刊物!不赚你们这些所谓文人的钱赚谁的钱!”
“这么说,我就是费尽心机在纸媒上发表出作品,也没几个人知道,也没人看?”
“当然了!”
“扑通”一声,甄老愚倒在了沙发上。他口吐白沫,两眼翻白,昏了过去。漂白粉毕竟见多识广,知道他这是精神受刺激太厉害,没有什么大问题,便上去逮住他的人中使劲儿掐。不一会儿,甄老鱼醒过来了,但两眼发直,没有任何表情,只是不住地说,完了,完了。他抓住漂白粉的手,在心里说,这真是一个好女人啊!二十多年来,全是她在养活我。发表文章需要订刊物,她又要掏腰包订购。作为一个大男人,叫一个小女子养活,实在太丢人了。至于戴绿帽子,更是绝大的耻辱。他自感欠漂白粉的太多,不愿意再往下低他那作为文人的高贵的头颅了。他从沙发上爬起来,骑上自己的那辆破自行车就要走。
“干啥去?”
“回去。”
“我用车送送你吧?”
“不用!”
当天夜里,甄老愚就在自己的住处上吊自杀了。得知消息后,漂白粉赶去料理他的后事。发现,在甄老愚电脑桌的台历上,工工整整地写有两个大字:绝望。

(作者简介:董攀山,山东定陶人,解放军某部政委。199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。爱好文学。先后在《时代文学》《中国老年》《祝你幸福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前卫报》《大众日报》等报刊和新媒体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千余篇。著有长篇纪实文学《我的军旅生涯》一书。)